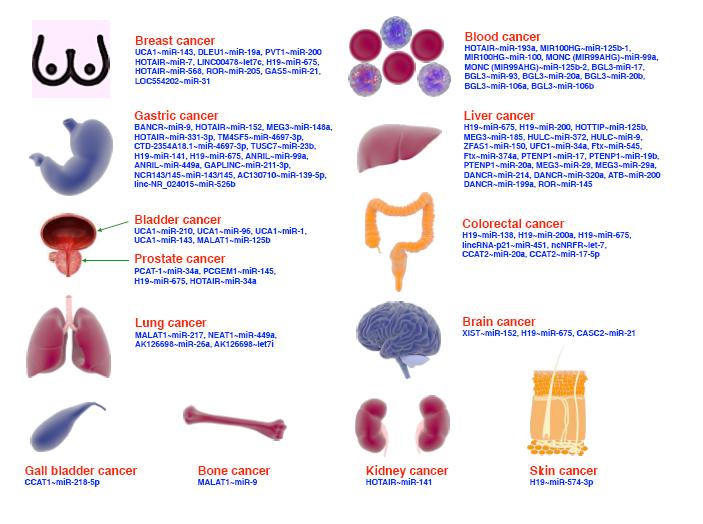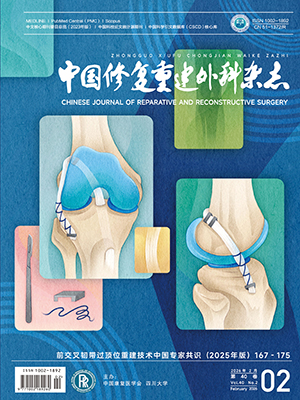- 1. Sports Medicine Institut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P.R.China;
- 2. Department of Sports Medicine, Hua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P.R.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ligament products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 surgeries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twisty way. In the 1970s, early artificial ligament products were initially used for ACL surgeries, which showed poor clinical efficacy and eventually ended up in failure.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number of ACL reconstruction with new artificial ligament products, including the Leeds-KeioTM, the LARSTM (Ligament Advanced Reinfocement System), and the Trevira HochfestTM. Among these new products, the LARSTM has been more commonly applied for ACL surgeries. Although these new artificial ligament products have goo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show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cumulative failure and complication rate, they still have limitations.
Citation: CHEN Tianwu, CHEN Shiyi. Artificial ligaments applied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pair and reconstruction: Current products and experience. Chinese Journal of Reparative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2020, 34(1): 1-9. doi: 10.7507/1002-1892.201908084 Copy
Copyright ?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Reparative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of West China Medical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 1. | Robson AM. Ruptured crucial ligaments and their repair by operation. Ann Surg, 1903, 37(5): 716-718. |
| 2. | Lange F. On artificial silk ligaments. Munch Med Wschr, 1907, 52: 834-836. |
| 3. | Corner EM. The exploration of the knee-joint: with some illustrative cases. Br J Surg, 1914, 2(6): 191-204. |
| 4. | Smith SA.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juries to the crucial ligaments. Br J Surg, 1918, 6(22): 176-189. |
| 5. | Crawford SN, Waterman BR, Lubowitz JH. Long-term failure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Arthroscopy, 2013, 29(9): 1566-1571. |
| 6. | Burnett QM 2nd, Fowler PJ.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historical overview. Orthop Clin North Am, 1985, 16(1): 143-157. |
| 7. | Funk FJ Jr. Synthetic ligaments. Current status. Clin Orthop Relat Res, 1987, (219): 107-111. |
| 8. |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ducument for the preparation of 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s and premarket approval applications for intra-articular prosthetic knee ligament devices [EB/OL]. (1997-12-27)[2019-11-11] https://www.fda.gov/media/72463/download. |
| 9. | Fujikawa K, Iseki F, Seedhom BB. Arthroscopy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Leeds-Keio ligament. J Bone Joint Surg (Br), 1989, 71(4): 566-570. |
| 10. | Matsumoto H, Fujikawa K. Leeds-Keio artificial ligament: a new concept for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knee. Keio J Med, 2001, 50(3): 161-166. |
| 11. | Getelman MH, Friedman MJ. Complications and pitfalls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with synthetic grafts//Malek MM. Knee Surgery: Complications, Pitfalls, and Salvage. Berlin: Springer, 2001: 113-120. |
| 12. | Murray AW, Macnicol MF. 10-16 year results of Leeds-Keio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Knee, 2004, 11(1): 9-14. |
| 13. | Macnicol MF, Penny ID, Sheppard L. Early results of the Leeds-Keio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placement. J Bone Joint Surg (Br), 1991, 73(3): 377-380. |
| 14. | Ghalayini SR, Helm AT, Bonshahi AY, et al. Arthroscopic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surgery: results of autogenous patellar tendon graft versus the Leeds-Keio synthetic graft five year follow-up of a prospectiv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Knee, 2010, 17(5): 334-339. |
| 15. | Engstr?m B, Wredmark T, Westblad P. Patellar tendon or Leeds-Keio graft i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uptures. Intermediate results. Clin Orthop Relat Res, 1993, (295): 190-197. |
| 16. | Nakayama Y, Shirai Y, Narita T, et al. Knee functions and a return to sports activity in competitive athletes following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J Nippon Med Sch, 2000, 67(3): 172-176. |
| 17. | Nakayama Y, Shirai Y, Narita T, et al. Remodeling of patellar tendon grafts augmented with woven polyester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in humans. J Orthop Sci, 1999, 4(3): 163-170. |
| 18. | Jones AP, Sidhom S, Sefton G. Long-term clinical review (10-20 years) aft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using the Leeds-Keio synthetic ligament. J Long Term Eff Med Implants, 2007, 17(1): 59-69. |
| 19. | Zaffagnini S, Marcheggiani Muccioli GM, Chatrath V, et al. Histolog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evaluation of Leeds-Keio ligament 20 years after implant: a case report. Knee Surg Sports Traumatol Arthrosc, 2008, 16(11): 1026-1029. |
| 20. | Sugihara A, Fujikawa K, Watanabe H, et al. Anterior cruciate reconstruction with bioactive Leeds-Keio ligament (LKⅡ): preliminary report. J Long Term Eff Med Implants, 2006, 16(1): 41-49. |
| 21. | Johnson D, Laboureau J.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with synthetics//Pos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ies. Berlin: Springer, 2001: 189-214. |
| 22. | Chen T, Zhang P, Chen J, et al. Long-term outcomes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either synthetics with remnant preservation or hamstring autografts: A 10-year longitudinal study. Am J Sports Med, 2017, 45(12): 2739-2750. |
| 23. | 郭新毅, 畢樹雄. 前交叉韌帶重建術治療急性與陳舊性前交叉韌帶損傷的療效研究. 中國藥物與臨床, 2017, 17(6): 876-879. |
| 24. | 丁國成, 劉銘, 項良碧, 等. 人工韌帶聯合自體肌腱在前交叉韌帶重建失敗后翻修手術中應用. 臨床軍醫雜志, 2017, 45(8): 809-812. |
| 25. | 孔穎, 王國棟, 張元民, 等. 前交叉韌帶重建失敗后的首次翻修.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 2014, 18(46): 7458-7462. |
| 26. | 黃建明, 沈鋒, 眭杰, 等. Segond 骨折的臨床特點與治療策略.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1, 26(6): 509-511. |
| 27. | 徐又佳, 沈光思, 董啟榕, 等. 術中 X 線透視定位行 LARS 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價值. 中華創傷雜志, 2011, 27(2): 141-145. |
| 28. | 王宇, 劉銘, 劉憲民, 等. 3D 打印股骨隧道精確定位法結合 LARS 人工韌帶移植在前交叉韌帶重建手術中應用. 臨床軍醫雜志, 2016, 44(10): 991-994. |
| 29. | 王洪震, 郝彥明, 賈正平, 等. 關節鏡結合 C 型臂機下用 LARS 人工韌帶治療膝關節前交叉韌帶斷裂的療效觀察. 山東醫藥, 2013, 53(17): 87-88, 98. |
| 30. | 黃長明, 沈瑞群, 范華強, 等. 關節鏡下解剖等長重建技術在 LARS 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中的應用.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07, 22(8): 647-649. |
| 31. | 劉憲民, 王琪, 劉松波, 等. LARS 韌帶在超常體重人群前交叉韌帶重建中的應用.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1, 26(10): 931-932. |
| 32. | 黃愛華. 關節鏡下膝關節前交叉韌帶斷裂人工韌帶重建的術中配合. 右江民族醫學院學報, 2011, 33(6): 880-881. |
| 33. | 張彥成. 關節鏡下應用自體韌帶與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手術配合//中華護理學會第 16 屆全國手術室護理學術交流會議論文集. 長沙: 中華護理學會. 2012. |
| 34. | 駱麗, 官曉慶, 曾俊,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手術配合. 護士進修雜志, 2010, 25(3): 262-263. |
| 35. | 何銳, 楊柳, 郭林, 等. 134 例 LARS 韌帶移植 ACL 重建術療效觀察與失敗原因分析//第二十四屆全國中西醫結合骨傷科學術年會論文集. 呼和浩特: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 2017. |
| 36. | 王立德, 于利, 張羽飛, 等.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關節交叉韌帶后再手術案例分析//第十八屆中國內鏡醫師大會論文集. 長沙: 中國醫師協會, 2018. |
| 37. | 齊志明, 王立德, 于利, 等.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初步體會. 中國微創外科雜志, 2005, 5(5): 364-366. |
| 38. | 吳宇黎, 吳海山, 李曉華, 等. LARS 人工韌帶在前交叉韌帶重建中的作用. 實用骨科雜志, 2007, 13(1): 4-6. |
| 39. | 王立德, 于利, 張衛國,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關節前十字韌帶損傷//第四屆上海國際關節鏡與運動醫學學術論壇論文集. 上海: 中國運動醫學學會, 2007. |
| 40. | 萬鈞, 溫鵬, 楊曉宇, 等. 關節鏡下 LARS 重建交叉韌帶的療效觀察. 寧夏醫學雜志, 2007, 29(12): 1072-1073. |
| 41. | 李歡, 高桂英, 何國礎, 等.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應用.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08, 23(1): 57-59. |
| 42. | 黃華揚, 鄭小飛, 張余,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42例.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 2008, 12(32): 6283-6286. |
| 43. | 符培亮, 吳海山, 李曉華, 等. LARS 人工韌帶移植重建膝關節前交叉韌帶 28 例.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 2008, 12(27): 5393-5396. |
| 44. | 陳明, 董啟榕.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加強系統重建前交叉韌帶.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 2008, 12(33): 6597-6600. |
| 45. | 徐又佳, 董啟榕, 周海濱, 等. 關節鏡下運用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 中國矯形外科雜志, 2008, 16(24): 1841-1844. |
| 46. | 張利恒, 桑平, 李光淳,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療效觀察. 吉林醫學, 2008, 29(23): 2148-2149. |
| 47. | 曹興海, 李志達, 涂大華,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關節前交叉韌帶的臨床應用. 廣東醫學院學報, 2009, 27(4): 419-420. |
| 48. | 李利南.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術后中期隨訪結果及分析. 大連: 大連醫科大學, 2009. |
| 49. | 黃偉, 張文濤, 張新濤,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在重建前交叉韌帶中的臨床應用. 臨床和實驗醫學雜志, 2010, 9(11): 816-817. |
| 50. | 張建林, 葉軍, 趙俊華, 等.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材料 LARS 韌帶重建急性前交叉韌帶損傷 23 例.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 2010, 14(16): 3011-3014. |
| 51. | 呂廷灼, 趙力, 張英劍, 等. LARS 人工韌帶重建急性交叉韌帶斷裂的療效分析. 天津醫藥, 2010, 38(12): 1108-1109. |
| 52. | 李棋, 唐新, 楊天府,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急性期前交叉韌帶損傷的臨床療效觀察. 中國骨傷, 2010, 23(12): 952-954. |
| 53. | 董偉強, 尹知訓, 白波, 等.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臨床研究. 國際醫藥衛生導報, 2011, 17(24): 3021-3024. |
| 54. | 譚志超, 蔡立民, 鄧懷東,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臨床觀察. 現代醫院, 2011, 11(2): 36-38. |
| 55. | 門宏亮. 應用 LARS 人工韌帶關節鏡下重建膝前交叉韌帶損傷的臨床療效觀察. 延吉: 延邊大學, 2012. |
| 56. | 陳曉磊, 汪漢民. 關節鏡微創技術在 ACL 重建中的應用及臨床分析. 中外醫療, 2013, 32(23): 75-76. |
| 57. | 張傳開, 馮暉, 孫燚炎,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臨床療效. 河北醫科大學學報, 2013, 34(8): 935-937. |
| 58. | 李利南, 張衛國, 王立德, 等. 韌帶增強重建系統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中期療效分析. 中華創傷雜志, 2013, 29(8): 756-761. |
| 59. | 孫永進.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后5年系列隨訪研究. 蘇州: 蘇州大學, 2013. |
| 60. | 王景靚, 徐曉峰. 人工韌帶關節鏡下重建膝前交叉韌帶治療體會//第二十一屆全國中西醫結合骨傷科學術研討會暨骨傷科分會換屆大會論文匯編. 天津: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 2014. |
| 61. | 袁擁軍, 何國礎, 孫長惠, 等. 關節鏡下先進人工韌帶加強系統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 5 年隨訪研究. 食品與藥品, 2014, 16(5): 311-315. |
| 62. | 成小輝, 劉偉峰. 40 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關節交叉韌帶的臨床治療體會. 現代診斷與治療, 2015, 26(11): 2563-2564. |
| 63. | 康一凡. 關節鏡下應用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關節交叉韌帶. 透析與人工器官, 2016, 27(2): 9-12. |
| 64. | 高鋒, 李銘章, 王洪偉,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臨床效果分析. 河南醫學研究, 2016, 25(7): 1238-1239. |
| 65. | 謝波, 李忠, 張忠杰, 等.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研究. 重慶醫學, 2016, 45(28): 3937-3939. |
| 66. | 吳國志. LARS 人工韌帶與自體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術后最少隨訪時間 7 年療效比較. 大連: 大連醫科大學, 2016. |
| 67. | 高玉鐳, 陳鳳梅, 張寅權, 等.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 8~10 年臨床報道.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6, 31(10): 1092-1093. |
| 68. | 林小福, 丁浩, 何建華,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臨床療效. 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 2017, 17(2): 199-200. |
| 69. | 王海明, 周自廣. 關節鏡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價值分析. 中國綜合臨床, 2018, 34(5): 449-451. |
| 70. | 方志峰.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療效分析. 中國衛生標準管理, 2018, 9(19): 82-84. |
| 71. | 曹印福.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 41 例療效分析. 中國醫藥指南, 2018, 16(3): 138-139. |
| 72. | 馬軍, 溫鵬, 牛東生,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中長期療效觀察. 寧夏醫學雜志, 2018, 40(10): 884-886. |
| 73. | 陳世益, 洪國威, 陳疾忤, 等. LARS 人工韌帶與自體腘繩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早期臨床療效比較. 中國運動醫學雜志, 2007, 26(5): 530-533. |
| 74. | 范欽波, 范繼峰. 關節鏡下先進人工韌帶加強系統和四股自體半腱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療效比較.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08, 22(6): 676-679. |
| 75. | 張兵. LARS 人工韌帶與自體腘繩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早期臨床療效比較. 遵義: 遵義醫學院, 2009. |
| 76. | 季振濤, 王少山.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及 4 股半腱肌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 臨床骨科雜志, 2011, 14(3): 268-270. |
| 77. | 胡慈貞, 阮慶平, 沈鋒, 等. LARS 人工韌帶與自體腘繩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康復護理及療效比較. 中國實用護理雜志, 2012, 28(23): 28-30. |
| 78. | 寧超. LARS 韌帶與自體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療效觀察. 濟南: 山東大學, 2012. |
| 79. | 范文斌, 趙建寧. 關節鏡下 LARS 韌帶與自體腘繩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早期臨床療效比較.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3, 28(7): 635-637. |
| 80. | 楊東方. LARS 人工韌帶與腘繩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效果對比: 3-8 年隨訪. 大連: 大連醫科大學, 2016. |
| 81. | 楊偉巍. LARS 韌帶與自體半腱-股薄肌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中長期臨床效果比較. 濟南: 山東大學, 2016. |
| 82. | 陳文祥, 謝煜, 包倪榮,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與自體腘繩肌腱對前交叉韌帶重建的早期療效比較. 醫學研究生學報, 2017, 30(2): 165-168. |
| 83. | 劉玉新, 李云, 張其亮, 等. 4 股腘繩肌腱與 LARS 人工韌帶重建治療急性 ACL 損傷早期療效比較.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7, 32(6): 634-636. |
| 84. | 施犇, 陳爍, 周立武, 等. 自體腘繩肌腱與 LARS 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中期療效比較. 中國矯形外科雜志, 2018, 26(16): 1441-1445. |
| 85. | 袁擁軍, 何國礎, 岑建平, 等. 先進人工韌帶加強系統人工韌帶與自體骨-髕腱-骨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早期臨床療效比較. 上海醫學, 2009, 32(7): 598-601. |
| 86. | 潘孝云, 溫宏, 王立德, 等. 自體骨-腱-骨移植物與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比較. 臨床骨科雜志, 2012, 15(5): 542-544. |
| 87. | 欒沖, 張才龍, 孫康,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與 γ 射線照射的同種異體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早期臨床療效比較. 中國矯形外科雜志, 2010, 18(10): 808-811. |
| 88. | 陸晴友, 王子彬, 袁鋒, 等. 三種不同移植物重建前交叉韌帶的療效分析.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09, 24(4): 295-297. |
| 89. | 王永祥.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與自體移植物重建前交叉韌帶(ACL)臨床效果對比研究. 呼和浩特: 內蒙古醫科大學, 2009. |
| 90. | 陳男, 董啟榕. 三種移植物關節鏡下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療效比較. 中國現代醫藥雜志, 2012, 14(12): 7-9. |
| 91. | 鄭小飛, 黃華揚, 張余, 等. 關節鏡下重建前交叉韌帶移植物的選擇與療效比較.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09, 24(7): 592-594. |
| 92. | Nau T, Lavoie P, Duval N. A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ligaments in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wo-year follow-up of a randomised trial. J Bone Joint Surg (Br), 2002, 84(3): 356-360. |
| 93. | Pan X, Wen H, Wang L, et al. Bone-patellar tendon-bone autograft versus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 fo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Eur J Orthop Surg Traumatol, 2013, 23(7): 819-823. |
| 94. | Liu ZT, Zhang XL, Jiang Y, et al. Four-strand hamstring tendon autograft versus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 fo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Int Orthop, 2010, 34(1): 45-49. |
| 95. | Gao K, Chen S, Wang L, et al.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with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 a multicenter study with 3- to 5-year follow-up. Arthroscopy, 2010, 26(4): 515-523. |
| 96. | Bianchi N, Sacchetti F, Bottai V, et al. LARS versus hamstring tendon autograft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a single-centre, single surgeon retrospective study with 8 years of follow-up. Eur J Orthop Surg Traumatol, 2019, 29(2): 447-453. |
| 97. | Hamido F, Al Harran H, Al Misfer AR, et al. Augmented short undersized hamstring tendon graft with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 versus four-strand hamstring tendon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preliminary results. Orthop Traumatol Surg Res, 2015, 101(5): 535-538. |
| 98. | Bugelli G, Dell’Osso G, Ascione F, et al. LARS in ACL reconstruction: evaluation of 60 cases with 5-year minimum follow-up. Musculoskelet Surg, 2018, 102(1): 57-62. |
| 99. | Chen J, Gu A, Jiang H, et al. A comparison of acute and chronic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s: a randomized prospective study with a 5-year follow-up. Arch Orthop Trauma Surg, 2015, 135(1): 95-102. |
| 100. | Hamido F, Misfer AK, Al Harran H, et al. The use of the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 to augment a short or undersized ACL hamstrings tendon graft. Knee, 2011, 18(6): 373-378. |
| 101. | Jia Z, Xue C, Wang W, et al. Clinical outcomes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LARS artificial graft with an at least 7-year follow-up. Medicine (Baltimore), 2017, 96(14): e6568. |
| 102. | Parchi PD, Gianluca C, Dolfi L, et al.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with LARSTM artificial ligament results at a mean follow-up of eight years. Int Orthop, 2013, 37(8): 1567-1574. |
| 103. | Su M, Jia X, Zhang Z, et al. Medium-term (least 5 years) comparative outcomes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4SHG, allograft, and LARS ligament. Clin J Sport Med, 2019. [Epub ahead of print]. |
| 104. | Tiefenboeck TM, Thurmaier E, Tiefenboeck MM, et al.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outcome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the LARSTM system at a minimum follow-up of 10 years. Knee, 2015, 22(6): 565-568. |
| 105. | Krudwig WK. Reconstruction of cruciate ligaments using a synthetic ligament of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Trevira Ligament)//YAHIA LH. Ligaments and ligamentoplasties. Berlin: Springer, 1997: 245-253. |
| 106. | Paessler HH, Deneke J, Dahners LE. Augmented repair and early mobilization of acut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ies. Am J Sports Med, 1992, 20(6): 667-674. |
| 107. | Kock HJ, Sturmer KM, Letsch R, et al. Interface and biocompatibility of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knee ligament prostheses. A histolog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device retrieval analysis in failed synthetic implants used for surgical repair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s. Arch Orthop Trauma Surg, 1994, 114(1): 1-7. |
| 108. | Letsch R, Sturmer KM, Kock HJ, et al. Replacement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by a PET prosthesis (Trevira extra-strength) as a salvage procedure in chronically unstable previously operated knee joints. Intermediate to long-term results of a clinical study. Unfallchirurgie, 1994, 20(6): 293-301. |
| 109. | Lubowitz JH, MacKay G, Gilmer B. Knee medial collateral ligament and posteromedial corner anatomic repair with internal bracing. Arthrosc Tech, 2014, 3(4): e505-e508. |
| 110. | Smith PA, Bley JA. Allograft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tilizing internal brace augmentation. Arthrosc Tech, 2016, 5(5): e1143-e1147. |
| 111. | Aboalata M, Elazab A, Halawa A, et al. Internal suture augmentation technique to protect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graft. Arthrosc Tech, 2017, 6(5): e1633-e1638. |
| 112. | Batty LM, Norsworthy CJ, Lash NJ, et al. Synthetic devices for reconstructive surgery of the cruciate ligam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rthroscopy, 2015, 31(5): 957-968. |
| 113. | Lubowitz JH. Editorial commentary: synthetic ACL graft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clinical nonbelievers may realize. Arthroscopy, 2015, 31(5): 969-970. |
| 114. | Waterman BR, Johnson DH. Synthetic grafts--Where is the common sense? Arthroscopy, 2015, 31(10): 1849-1850. |
| 115. | Brulez B. Synthetic Grafts. Arthroscopy, 2016, 32(4): 543. |
- 1. Robson AM. Ruptured crucial ligaments and their repair by operation. Ann Surg, 1903, 37(5): 716-718.
- 2. Lange F. On artificial silk ligaments. Munch Med Wschr, 1907, 52: 834-836.
- 3. Corner EM. The exploration of the knee-joint: with some illustrative cases. Br J Surg, 1914, 2(6): 191-204.
- 4. Smith SA.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juries to the crucial ligaments. Br J Surg, 1918, 6(22): 176-189.
- 5. Crawford SN, Waterman BR, Lubowitz JH. Long-term failure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Arthroscopy, 2013, 29(9): 1566-1571.
- 6. Burnett QM 2nd, Fowler PJ.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historical overview. Orthop Clin North Am, 1985, 16(1): 143-157.
- 7. Funk FJ Jr. Synthetic ligaments. Current status. Clin Orthop Relat Res, 1987, (219): 107-111.
- 8.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ducument for the preparation of 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s and premarket approval applications for intra-articular prosthetic knee ligament devices [EB/OL]. (1997-12-27)[2019-11-11] https://www.fda.gov/media/72463/download.
- 9. Fujikawa K, Iseki F, Seedhom BB. Arthroscopy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Leeds-Keio ligament. J Bone Joint Surg (Br), 1989, 71(4): 566-570.
- 10. Matsumoto H, Fujikawa K. Leeds-Keio artificial ligament: a new concept for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knee. Keio J Med, 2001, 50(3): 161-166.
- 11. Getelman MH, Friedman MJ. Complications and pitfalls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with synthetic grafts//Malek MM. Knee Surgery: Complications, Pitfalls, and Salvage. Berlin: Springer, 2001: 113-120.
- 12. Murray AW, Macnicol MF. 10-16 year results of Leeds-Keio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Knee, 2004, 11(1): 9-14.
- 13. Macnicol MF, Penny ID, Sheppard L. Early results of the Leeds-Keio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placement. J Bone Joint Surg (Br), 1991, 73(3): 377-380.
- 14. Ghalayini SR, Helm AT, Bonshahi AY, et al. Arthroscopic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surgery: results of autogenous patellar tendon graft versus the Leeds-Keio synthetic graft five year follow-up of a prospectiv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Knee, 2010, 17(5): 334-339.
- 15. Engstr?m B, Wredmark T, Westblad P. Patellar tendon or Leeds-Keio graft i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uptures. Intermediate results. Clin Orthop Relat Res, 1993, (295): 190-197.
- 16. Nakayama Y, Shirai Y, Narita T, et al. Knee functions and a return to sports activity in competitive athletes following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J Nippon Med Sch, 2000, 67(3): 172-176.
- 17. Nakayama Y, Shirai Y, Narita T, et al. Remodeling of patellar tendon grafts augmented with woven polyester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in humans. J Orthop Sci, 1999, 4(3): 163-170.
- 18. Jones AP, Sidhom S, Sefton G. Long-term clinical review (10-20 years) aft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using the Leeds-Keio synthetic ligament. J Long Term Eff Med Implants, 2007, 17(1): 59-69.
- 19. Zaffagnini S, Marcheggiani Muccioli GM, Chatrath V, et al. Histolog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evaluation of Leeds-Keio ligament 20 years after implant: a case report. Knee Surg Sports Traumatol Arthrosc, 2008, 16(11): 1026-1029.
- 20. Sugihara A, Fujikawa K, Watanabe H, et al. Anterior cruciate reconstruction with bioactive Leeds-Keio ligament (LKⅡ): preliminary report. J Long Term Eff Med Implants, 2006, 16(1): 41-49.
- 21. Johnson D, Laboureau J.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with synthetics//Pos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ies. Berlin: Springer, 2001: 189-214.
- 22. Chen T, Zhang P, Chen J, et al. Long-term outcomes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either synthetics with remnant preservation or hamstring autografts: A 10-year longitudinal study. Am J Sports Med, 2017, 45(12): 2739-2750.
- 23. 郭新毅, 畢樹雄. 前交叉韌帶重建術治療急性與陳舊性前交叉韌帶損傷的療效研究. 中國藥物與臨床, 2017, 17(6): 876-879.
- 24. 丁國成, 劉銘, 項良碧, 等. 人工韌帶聯合自體肌腱在前交叉韌帶重建失敗后翻修手術中應用. 臨床軍醫雜志, 2017, 45(8): 809-812.
- 25. 孔穎, 王國棟, 張元民, 等. 前交叉韌帶重建失敗后的首次翻修.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 2014, 18(46): 7458-7462.
- 26. 黃建明, 沈鋒, 眭杰, 等. Segond 骨折的臨床特點與治療策略.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1, 26(6): 509-511.
- 27. 徐又佳, 沈光思, 董啟榕, 等. 術中 X 線透視定位行 LARS 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價值. 中華創傷雜志, 2011, 27(2): 141-145.
- 28. 王宇, 劉銘, 劉憲民, 等. 3D 打印股骨隧道精確定位法結合 LARS 人工韌帶移植在前交叉韌帶重建手術中應用. 臨床軍醫雜志, 2016, 44(10): 991-994.
- 29. 王洪震, 郝彥明, 賈正平, 等. 關節鏡結合 C 型臂機下用 LARS 人工韌帶治療膝關節前交叉韌帶斷裂的療效觀察. 山東醫藥, 2013, 53(17): 87-88, 98.
- 30. 黃長明, 沈瑞群, 范華強, 等. 關節鏡下解剖等長重建技術在 LARS 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中的應用.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07, 22(8): 647-649.
- 31. 劉憲民, 王琪, 劉松波, 等. LARS 韌帶在超常體重人群前交叉韌帶重建中的應用.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1, 26(10): 931-932.
- 32. 黃愛華. 關節鏡下膝關節前交叉韌帶斷裂人工韌帶重建的術中配合. 右江民族醫學院學報, 2011, 33(6): 880-881.
- 33. 張彥成. 關節鏡下應用自體韌帶與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手術配合//中華護理學會第 16 屆全國手術室護理學術交流會議論文集. 長沙: 中華護理學會. 2012.
- 34. 駱麗, 官曉慶, 曾俊,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手術配合. 護士進修雜志, 2010, 25(3): 262-263.
- 35. 何銳, 楊柳, 郭林, 等. 134 例 LARS 韌帶移植 ACL 重建術療效觀察與失敗原因分析//第二十四屆全國中西醫結合骨傷科學術年會論文集. 呼和浩特: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 2017.
- 36. 王立德, 于利, 張羽飛, 等.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關節交叉韌帶后再手術案例分析//第十八屆中國內鏡醫師大會論文集. 長沙: 中國醫師協會, 2018.
- 37. 齊志明, 王立德, 于利, 等.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初步體會. 中國微創外科雜志, 2005, 5(5): 364-366.
- 38. 吳宇黎, 吳海山, 李曉華, 等. LARS 人工韌帶在前交叉韌帶重建中的作用. 實用骨科雜志, 2007, 13(1): 4-6.
- 39. 王立德, 于利, 張衛國,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關節前十字韌帶損傷//第四屆上海國際關節鏡與運動醫學學術論壇論文集. 上海: 中國運動醫學學會, 2007.
- 40. 萬鈞, 溫鵬, 楊曉宇, 等. 關節鏡下 LARS 重建交叉韌帶的療效觀察. 寧夏醫學雜志, 2007, 29(12): 1072-1073.
- 41. 李歡, 高桂英, 何國礎, 等.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應用.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08, 23(1): 57-59.
- 42. 黃華揚, 鄭小飛, 張余,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42例.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 2008, 12(32): 6283-6286.
- 43. 符培亮, 吳海山, 李曉華, 等. LARS 人工韌帶移植重建膝關節前交叉韌帶 28 例.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 2008, 12(27): 5393-5396.
- 44. 陳明, 董啟榕.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加強系統重建前交叉韌帶.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 2008, 12(33): 6597-6600.
- 45. 徐又佳, 董啟榕, 周海濱, 等. 關節鏡下運用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 中國矯形外科雜志, 2008, 16(24): 1841-1844.
- 46. 張利恒, 桑平, 李光淳,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療效觀察. 吉林醫學, 2008, 29(23): 2148-2149.
- 47. 曹興海, 李志達, 涂大華,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關節前交叉韌帶的臨床應用. 廣東醫學院學報, 2009, 27(4): 419-420.
- 48. 李利南.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術后中期隨訪結果及分析. 大連: 大連醫科大學, 2009.
- 49. 黃偉, 張文濤, 張新濤,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在重建前交叉韌帶中的臨床應用. 臨床和實驗醫學雜志, 2010, 9(11): 816-817.
- 50. 張建林, 葉軍, 趙俊華, 等.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材料 LARS 韌帶重建急性前交叉韌帶損傷 23 例.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床康復, 2010, 14(16): 3011-3014.
- 51. 呂廷灼, 趙力, 張英劍, 等. LARS 人工韌帶重建急性交叉韌帶斷裂的療效分析. 天津醫藥, 2010, 38(12): 1108-1109.
- 52. 李棋, 唐新, 楊天府,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急性期前交叉韌帶損傷的臨床療效觀察. 中國骨傷, 2010, 23(12): 952-954.
- 53. 董偉強, 尹知訓, 白波, 等.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臨床研究. 國際醫藥衛生導報, 2011, 17(24): 3021-3024.
- 54. 譚志超, 蔡立民, 鄧懷東,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臨床觀察. 現代醫院, 2011, 11(2): 36-38.
- 55. 門宏亮. 應用 LARS 人工韌帶關節鏡下重建膝前交叉韌帶損傷的臨床療效觀察. 延吉: 延邊大學, 2012.
- 56. 陳曉磊, 汪漢民. 關節鏡微創技術在 ACL 重建中的應用及臨床分析. 中外醫療, 2013, 32(23): 75-76.
- 57. 張傳開, 馮暉, 孫燚炎,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臨床療效. 河北醫科大學學報, 2013, 34(8): 935-937.
- 58. 李利南, 張衛國, 王立德, 等. 韌帶增強重建系統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中期療效分析. 中華創傷雜志, 2013, 29(8): 756-761.
- 59. 孫永進.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后5年系列隨訪研究. 蘇州: 蘇州大學, 2013.
- 60. 王景靚, 徐曉峰. 人工韌帶關節鏡下重建膝前交叉韌帶治療體會//第二十一屆全國中西醫結合骨傷科學術研討會暨骨傷科分會換屆大會論文匯編. 天津: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 2014.
- 61. 袁擁軍, 何國礎, 孫長惠, 等. 關節鏡下先進人工韌帶加強系統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 5 年隨訪研究. 食品與藥品, 2014, 16(5): 311-315.
- 62. 成小輝, 劉偉峰. 40 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關節交叉韌帶的臨床治療體會. 現代診斷與治療, 2015, 26(11): 2563-2564.
- 63. 康一凡. 關節鏡下應用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關節交叉韌帶. 透析與人工器官, 2016, 27(2): 9-12.
- 64. 高鋒, 李銘章, 王洪偉,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臨床效果分析. 河南醫學研究, 2016, 25(7): 1238-1239.
- 65. 謝波, 李忠, 張忠杰, 等.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研究. 重慶醫學, 2016, 45(28): 3937-3939.
- 66. 吳國志. LARS 人工韌帶與自體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術后最少隨訪時間 7 年療效比較. 大連: 大連醫科大學, 2016.
- 67. 高玉鐳, 陳鳳梅, 張寅權, 等.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 8~10 年臨床報道.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6, 31(10): 1092-1093.
- 68. 林小福, 丁浩, 何建華,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臨床療效. 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 2017, 17(2): 199-200.
- 69. 王海明, 周自廣. 關節鏡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價值分析. 中國綜合臨床, 2018, 34(5): 449-451.
- 70. 方志峰.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療效分析. 中國衛生標準管理, 2018, 9(19): 82-84.
- 71. 曹印福.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 41 例療效分析. 中國醫藥指南, 2018, 16(3): 138-139.
- 72. 馬軍, 溫鵬, 牛東生,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中長期療效觀察. 寧夏醫學雜志, 2018, 40(10): 884-886.
- 73. 陳世益, 洪國威, 陳疾忤, 等. LARS 人工韌帶與自體腘繩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早期臨床療效比較. 中國運動醫學雜志, 2007, 26(5): 530-533.
- 74. 范欽波, 范繼峰. 關節鏡下先進人工韌帶加強系統和四股自體半腱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療效比較.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08, 22(6): 676-679.
- 75. 張兵. LARS 人工韌帶與自體腘繩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早期臨床療效比較. 遵義: 遵義醫學院, 2009.
- 76. 季振濤, 王少山.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及 4 股半腱肌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 臨床骨科雜志, 2011, 14(3): 268-270.
- 77. 胡慈貞, 阮慶平, 沈鋒, 等. LARS 人工韌帶與自體腘繩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康復護理及療效比較. 中國實用護理雜志, 2012, 28(23): 28-30.
- 78. 寧超. LARS 韌帶與自體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療效觀察. 濟南: 山東大學, 2012.
- 79. 范文斌, 趙建寧. 關節鏡下 LARS 韌帶與自體腘繩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早期臨床療效比較.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3, 28(7): 635-637.
- 80. 楊東方. LARS 人工韌帶與腘繩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效果對比: 3-8 年隨訪. 大連: 大連醫科大學, 2016.
- 81. 楊偉巍. LARS 韌帶與自體半腱-股薄肌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中長期臨床效果比較. 濟南: 山東大學, 2016.
- 82. 陳文祥, 謝煜, 包倪榮,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與自體腘繩肌腱對前交叉韌帶重建的早期療效比較. 醫學研究生學報, 2017, 30(2): 165-168.
- 83. 劉玉新, 李云, 張其亮, 等. 4 股腘繩肌腱與 LARS 人工韌帶重建治療急性 ACL 損傷早期療效比較.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7, 32(6): 634-636.
- 84. 施犇, 陳爍, 周立武, 等. 自體腘繩肌腱與 LARS 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中期療效比較. 中國矯形外科雜志, 2018, 26(16): 1441-1445.
- 85. 袁擁軍, 何國礎, 岑建平, 等. 先進人工韌帶加強系統人工韌帶與自體骨-髕腱-骨重建膝前交叉韌帶的早期臨床療效比較. 上海醫學, 2009, 32(7): 598-601.
- 86. 潘孝云, 溫宏, 王立德, 等. 自體骨-腱-骨移植物與 LARS 人工韌帶重建前交叉韌帶的比較. 臨床骨科雜志, 2012, 15(5): 542-544.
- 87. 欒沖, 張才龍, 孫康, 等. 關節鏡下 LARS 人工韌帶與 γ 射線照射的同種異體肌腱重建前交叉韌帶早期臨床療效比較. 中國矯形外科雜志, 2010, 18(10): 808-811.
- 88. 陸晴友, 王子彬, 袁鋒, 等. 三種不同移植物重建前交叉韌帶的療效分析.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09, 24(4): 295-297.
- 89. 王永祥. 關節鏡下人工韌帶與自體移植物重建前交叉韌帶(ACL)臨床效果對比研究. 呼和浩特: 內蒙古醫科大學, 2009.
- 90. 陳男, 董啟榕. 三種移植物關節鏡下重建前交叉韌帶的臨床療效比較. 中國現代醫藥雜志, 2012, 14(12): 7-9.
- 91. 鄭小飛, 黃華揚, 張余, 等. 關節鏡下重建前交叉韌帶移植物的選擇與療效比較.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09, 24(7): 592-594.
- 92. Nau T, Lavoie P, Duval N. A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ligaments in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wo-year follow-up of a randomised trial. J Bone Joint Surg (Br), 2002, 84(3): 356-360.
- 93. Pan X, Wen H, Wang L, et al. Bone-patellar tendon-bone autograft versus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 fo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Eur J Orthop Surg Traumatol, 2013, 23(7): 819-823.
- 94. Liu ZT, Zhang XL, Jiang Y, et al. Four-strand hamstring tendon autograft versus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 fo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Int Orthop, 2010, 34(1): 45-49.
- 95. Gao K, Chen S, Wang L, et al.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with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 a multicenter study with 3- to 5-year follow-up. Arthroscopy, 2010, 26(4): 515-523.
- 96. Bianchi N, Sacchetti F, Bottai V, et al. LARS versus hamstring tendon autograft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a single-centre, single surgeon retrospective study with 8 years of follow-up. Eur J Orthop Surg Traumatol, 2019, 29(2): 447-453.
- 97. Hamido F, Al Harran H, Al Misfer AR, et al. Augmented short undersized hamstring tendon graft with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 versus four-strand hamstring tendon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preliminary results. Orthop Traumatol Surg Res, 2015, 101(5): 535-538.
- 98. Bugelli G, Dell’Osso G, Ascione F, et al. LARS in ACL reconstruction: evaluation of 60 cases with 5-year minimum follow-up. Musculoskelet Surg, 2018, 102(1): 57-62.
- 99. Chen J, Gu A, Jiang H, et al. A comparison of acute and chronic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s: a randomized prospective study with a 5-year follow-up. Arch Orthop Trauma Surg, 2015, 135(1): 95-102.
- 100. Hamido F, Misfer AK, Al Harran H, et al. The use of the LARS artificial ligament to augment a short or undersized ACL hamstrings tendon graft. Knee, 2011, 18(6): 373-378.
- 101. Jia Z, Xue C, Wang W, et al. Clinical outcomes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LARS artificial graft with an at least 7-year follow-up. Medicine (Baltimore), 2017, 96(14): e6568.
- 102. Parchi PD, Gianluca C, Dolfi L, et al.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with LARSTM artificial ligament results at a mean follow-up of eight years. Int Orthop, 2013, 37(8): 1567-1574.
- 103. Su M, Jia X, Zhang Z, et al. Medium-term (least 5 years) comparative outcomes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4SHG, allograft, and LARS ligament. Clin J Sport Med, 2019. [Epub ahead of print].
- 104. Tiefenboeck TM, Thurmaier E, Tiefenboeck MM, et al.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outcome after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the LARSTM system at a minimum follow-up of 10 years. Knee, 2015, 22(6): 565-568.
- 105. Krudwig WK. Reconstruction of cruciate ligaments using a synthetic ligament of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Trevira Ligament)//YAHIA LH. Ligaments and ligamentoplasties. Berlin: Springer, 1997: 245-253.
- 106. Paessler HH, Deneke J, Dahners LE. Augmented repair and early mobilization of acut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ies. Am J Sports Med, 1992, 20(6): 667-674.
- 107. Kock HJ, Sturmer KM, Letsch R, et al. Interface and biocompatibility of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knee ligament prostheses. A histolog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device retrieval analysis in failed synthetic implants used for surgical repair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s. Arch Orthop Trauma Surg, 1994, 114(1): 1-7.
- 108. Letsch R, Sturmer KM, Kock HJ, et al. Replacement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by a PET prosthesis (Trevira extra-strength) as a salvage procedure in chronically unstable previously operated knee joints. Intermediate to long-term results of a clinical study. Unfallchirurgie, 1994, 20(6): 293-301.
- 109. Lubowitz JH, MacKay G, Gilmer B. Knee medial collateral ligament and posteromedial corner anatomic repair with internal bracing. Arthrosc Tech, 2014, 3(4): e505-e508.
- 110. Smith PA, Bley JA. Allograft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tilizing internal brace augmentation. Arthrosc Tech, 2016, 5(5): e1143-e1147.
- 111. Aboalata M, Elazab A, Halawa A, et al. Internal suture augmentation technique to protect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graft. Arthrosc Tech, 2017, 6(5): e1633-e1638.
- 112. Batty LM, Norsworthy CJ, Lash NJ, et al. Synthetic devices for reconstructive surgery of the cruciate ligam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rthroscopy, 2015, 31(5): 957-968.
- 113. Lubowitz JH. Editorial commentary: synthetic ACL graft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clinical nonbelievers may realize. Arthroscopy, 2015, 31(5): 969-970.
- 114. Waterman BR, Johnson DH. Synthetic grafts--Where is the common sense? Arthroscopy, 2015, 31(10): 1849-1850.
- 115. Brulez B. Synthetic Grafts. Arthroscopy, 2016, 32(4): 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