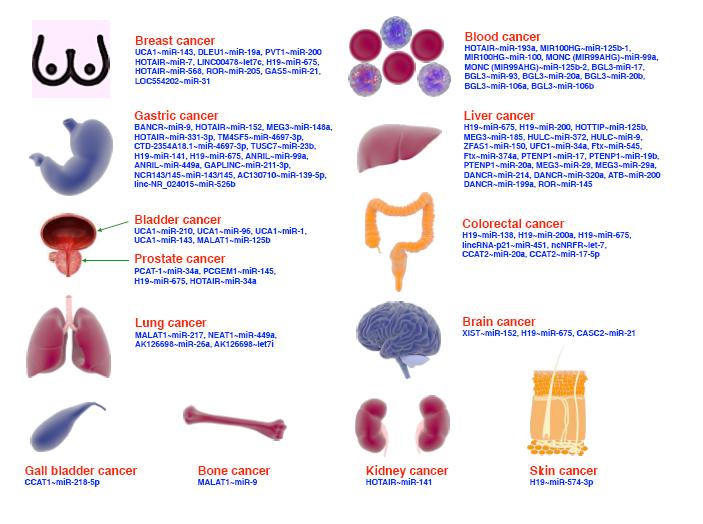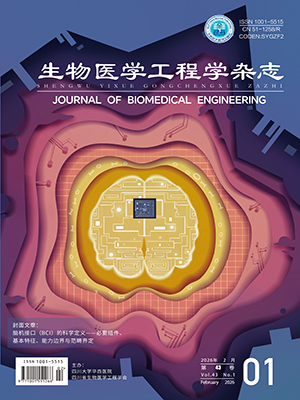| 1. |
Moser M B, Colgin L L, Igarashi K M, et al. Coordination of entorhinal-hippocampal ensemble activity during associative learning. Nature, 2014, 510(7503): 143-147.
|
| 2. |
Burak Y, Fiete I R, Sporns O. Accurate path integration in continuous attractor network models of grid cells. PLoS Comput Biol, 2008, 5(2): e1000291.
|
| 3. |
Bolding K A, Ferbinteanu J, Fox S E, et al. Place cell firing cannot support navigation without intact septal circuits. Hippocampus, 2020, 30(3): 175-191.
|
| 4. |
O’Keefe J, Dostrovsky J. The hippocampus as a spatial map.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unit activity in the freely-moving rat. Brain Res, 1971, 34(1): 171-175.
|
| 5. |
Wagatsuma H, Yamaguchi Y. Neural dynamics of the cognitive map in the hippocampus. Cogn Neurodyn, 2007, 1(2): 119-141.
|
| 6. |
Li T Y, Arleo A, Sheynikhovich D. Modeling place cells and grid cells in multi-compartment environments: Entorhinal–hippocampal loop as a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 circuit. Neural Netw, 2020, 121: 37-51.
|
| 7. |
Taube J S, Muller R U, Ranck J B. Head-direction cells recorded from the postsubiculum in freely moving rats. J Neurosci, 1990, 10(2): 420-435.
|
| 8. |
Muller R U, Ranck J B, Taube J S. Head direction cells: properties and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Curr Opin Neurobiol, 1996, 6(2): 196-206.
|
| 9. |
Kropff E, Carmichael J E, Moser M B, et al. Speed cells in the medial entorhinal cortex. Nature, 2015, 523(7561): 419-424.
|
| 10. |
于乃功, 苑云鶴, 李倜, 等. 一種基于海馬認知機理的仿生機器人認知地圖構建方法. 自動化學報, 2018, 44(1): 52-73.
|
| 11. |
Krupic J, Burgess N, O’Keefe J. 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location composed of spatially periodic bands. Science, 2012, 337(6096): 853-857.
|
| 12. |
McNaughton B L, Battaglia F P, Jensen O, et al. Path integration and the neural basis of the ‘cognitive map’. Nat Rev Neurosci, 2006, 7(8): 663-678.
|
| 13. |
Moser E I, Roudi Y, Witter M P, et al. Grid cells and cortical representation. Nat Rev Neurosci, 2014, 15(7): 466-481.
|
| 14. |
Moser E I, Kropff E, Moser M B. Place cells, grid cells, and the brain’s spati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Annu Rev Neurosci, 2008, 31(1): 69-89.
|
| 15. |
Wang Y H, Xu X Y, Pan X C, et al. Grid cell activity and path integration on 2-D manifolds in 3-D space. Nonlinear Dyn, 2021, 104(2): 1767-1780.
|
| 16. |
Burgess N, Barry C, O’Keefe J. An oscillatory interference model of grid cell firing. Hippocampus, 2010, 17(9): 801-812.
|
| 17. |
Erdem U M, Hasselmo M. A goal-directed spatial navigation model using forward trajectory planning based on grid cells. Eur J Neurosci, 2012, 35(6): 916-931.
|
| 18. |
Si B L, Romani S, Tsodyks M, et al. Continuous attractor network model for conjunctive position-by-velocity tuning of grid cells. PLoS Comput Biol, 2014, 10(4): e1003558.
|
| 19. |
Stepanyuk A. Self-organization of grid fields under supervision of place cells in the model of neuron with associative plasticity. Biol Inspired Cogn Archit, 2015, 13: 48-62.
|
| 20. |
Kang L, Balasubramanian V. A geometric attractor mechanism for self-organization of entorhinal grid modules. eLife, 2019, 8: e46687.
|
| 21. |
Cheng S, Frank L M. The structure of networks that produc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grid cells to place cells. Neuroscience, 2011, 197: 293-306.
|
| 22. |
Solstad T, Moser E I, Einevoll G T. From grid cells to place cells: A mathematical model. Hippocampus, 2006, 16(12): 1026-1031.
|
| 23. |
Bush D, Barry C, Burgess N. What do grid cells contribute to place cell firing?. Trends Neurosci, 2014, 37(3): 136-145.
|
| 24. |
于乃功, 廖詣深, 鄭相國. 一種基于海馬位置細胞選擇機制的空間認知模型. 生物醫學工程學雜志, 2020, 37(1): 27-37.
|
| 25. |
周陽, 吳德偉. 基于網格細胞到位置細胞轉換的位置估計模型. 電子與信息學報, 2017, 39(9): 2272-2276.
|
| 26. |
Rolls E T, Stringer S M, Elliot T. Entorhinal cortex grid cells can map to hippocampal place cells by competitive learning. Network Comp Neural, 2006, 17(4): 447-465.
|
| 27. |
于乃功, 王琳, 李倜, 等. 網格細胞到位置細胞的競爭型神經網絡模型. 控制與決策, 2015, 30(8): 1372-1378.
|
| 28. |
Milford M J, Wyeth G F. Mapping a suburb with a single camera using a biologically inspired SLAM system. IEEE Trans Robot, 2008, 24(5): 1038-1053.
|
| 29. |
Ball D, Heath S, Wiles J, et al. OpenRatSLAM: an open source brain-based SLAM system. Auton Robot, 2013, 34(3): 149-176.
|
| 30. |
Yu F W, Shang J G, Hu Y J, et al. NeuroSLAM: a brain-inspired slam system for 3D environments. Biol Cybern, 2019, 113(5-6): 515-545.
|
| 31. |
Zou Q, Cong M, Liu D, et al. Robotic episodic cognitive learning inspired by hippocampal spatial cells. IEEE Robot Autom Lett, 2020, 5(4): 5573-5580.
|
| 32. |
李偉龍, 吳德偉, 盧虎, 等. 一種閾值動態調整的仿生同步自主定位方法.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 2017, 51(10): 100-106.
|
| 33. |
Rumelhart D E, Hinton G E, Williams R J.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by back propagating errors. Nature, 1986, 323(6088): 533-536.
|
| 34. |
Hafting T, Fyhn M, Molden S, et al. Microstructure of a spatial map in the entorhinal cortex. Nature, 2005, 436(7052): 801-806.
|